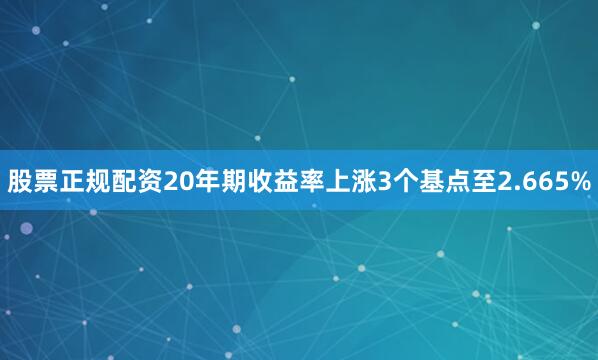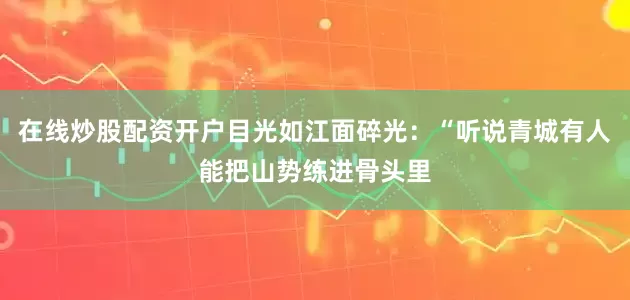
——岷江之秋,水声与骨节共筑长堤
一、秋水骤至
九月末,岷江上游连夜雨,水声从遥远的雪山一路滚落,像无数铁骑踏碎石涧。青城山脚的稻田刚收,稻茬还未来得及翻进泥里,便被一层浑浊的浪沫淹没。
铿站在村口老皂荚树下,手里攥着炎赠他的《连山易》简图。图上墨迹被雨水晕开,只剩“坎为水”三字仍清晰。他抬头望,乌云压得很低,仿佛伸手就能摸到湿冷的云底。
玄女冒雨跑来,发梢滴水:“尧帝与禹已至江上游,征调沿岸各部协力筑堤。广成子先生说,此非一人之力可成,让我们去听听水怎么说。”
铿点头,心里却像被水拍了一下——他从未见过如此急躁的岷江。
展开剩余82%二、初遇尧禹
溯江三十里,至一处回水湾。尧帝布衣麻履,鬓发斑白,正弯腰以手探水,像在给一位老友把脉。禹赤足立于江心巨石,裤腿卷至大腿,手执一根削尖的青冈棍,在石上刻一道又一道水痕。
铿上前施礼。禹回头,目光如江面碎光:“听说青城有人能把山势练进骨头里,可愿借我一用?”
铿笑:“骨头可以,山势得看江允不允许。”
尧帝闻言大笑,指着江面:“今日水位比昨夕高一寸三分,再涨两寸,便淹至丹棱稻田。我与禹欲在此筑半月堤,引洪入沱,但需千人扛石、千人挖沟。你带青城人来,我教你们在水里呼吸。”
铿心里一动:在水里呼吸,不是神通,而是学会与水同节奏。
三、石与肉的堤
次日,青城村青壮五十人,妇女三十人,背着藤筐、木杠、竹缆抵达工地。广成子没来,只让玄女带来一句话:“水不与人斗,人也不与水斗,只是帮水找一条更舒服的路。”
禹分派活计:
铿领二十人扛石,专挑棱角分明的“虎口石”,卡在堤基,让水咬不住;
玄女带妇女编藤网,盛碎石作“鱼鳞堰”,层层叠压,透水不溃;
尧帝则蹲在江边,以耳贴木桩,听水拍节奏,嘴里低声哼着一种古怪调子,像母亲拍婴孩入睡。
铿把赤足伸进冰凉的洪水,脚底卵石滚过,仿佛大地在换牙。他学着禹,屈膝、沉胯、肩与石平,石头的重量顺着脊背滑到脚跟,再被水轻轻托住。扛第三块时,他忽然听见自己髋骨“咔”一声,像榫头入槽,疼痛过后竟是一阵松快。
玄女在不远处编网,手指穿梭,嘴里轻轻数:“一纬一疏,水去不留;一扣一松,石稳如山。”她的声音混着江风,飘到铿耳里,竟与尧帝的调子合拍。
四、夜半试堤
第七日,堤高及腰。夜里忽起西风,浪头如奔马,直扑新堤。铿与禹巡堤,见一段藤网被撕开,水正灌入。
禹不喊人,只把手中青冈棍横插入决口,背对浪头,双脚像钉子一样钉进泥里。铿学着,用肩抵住棍尾,刹那间,一股巨力从棍身传来,胸骨几乎被压扁。他想起炎教他的“艮覆碗”,肩背一松一紧,力被分成两股,一股顺腿入地,一股沿臂回弹。浪头扑来,竟被弹出一道白沫。
片刻,众人赶来填石。决口合拢,禹抹一把脸上的水,对铿笑:“刚才那一下,是你的山,还是我的山?”
铿喘着答:“是岷江的山。”
五、雨后心堤
雨停那日,秋阳像洗净的铜镜。堤成,水被驯服,乖乖拐进沱沟。岸边稻田露出半截稻茬,白鹭落下,长腿如竹枝点破镜面。
尧帝与禹坐在堤头,赤足垂水。铿与玄女捧来新蒸的稻饭,饭香混着泥土味。尧帝夹一筷,点头:“米里有石头的腥,也有汗水的咸,好吃。”
禹指给铿看江心漩涡:“水本无心,人心若稳,水亦稳。你刚才扛石时,心跳与水跳同拍,那便是堤。”
铿低头,看自己掌心:茧更厚,纹路却更清晰,像被水重新雕刻。
六、解缆归山
傍晚,青城人收工返乡。铿背篓里多了一块禹刻字的青冈棍,上写“水行其道,人立其岸”。玄女腰间挂一只尧帝送的陶哨,说是日后若洪水再来,一吹众即至。
归途,山色被晚霞一层层染透,溪水在石间跳,声音比来时轻。铿忽然想起广成子的话:“功夫不在招式,在明白何时该使什么劲。”
他回头望,新堤如一条静卧的龙,龙脊上,白鹭点点。
七、尾声
回到青城村,铿把青冈棍插在溪边,每日晨昏,对着岷江上游吹哨。哨音未响,山鸟先起,溪水先应。
玄女问他:“下次洪水,还扛得动吗?”
铿笑:“扛得动的,是这块石头;扛不动的,是整条江。我只要和水商量好,让它别冲我家门口就行。”
风过,稻茬沙沙,像岷江在远处鼓掌。
发布于:重庆市华夏配资网-配资炒股首选-股票配资公司行业门户-最新上线配资app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